运动品牌成长烦恼:lululemon低谷与新品牌狂飙
运动品牌成长面临烦恼,lululemon经历低谷,新品牌则呈现狂飙态势,摘要中简要概述了运动品牌所面临的挑战,包括老牌品牌如何走出低谷以及新品牌的迅速崛起,通过关注这些品牌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到运动品牌市场的动态变化和挑战。
消费行业有条做品牌的方法论是,你需要找个尽可能细分的切口、面对尽可能细分人群提供产品和服务。但关于品牌从0到1、从1到10闯出来之后,怎么继续保持增长却成了难题。
lululemon就碰到了这样的困境,它靠给super girl提供瑜伽裤起家,还成了全球第三大百亿美元单一运动品牌,规模仅次于耐克和阿迪达斯。
但因为新晋品牌的冲击,以及在扩张品类和人群的过程中不再独特,lululemon正在经历增速见顶,股价降到了过去62月以来的新低。
伴随lululemon的潮起潮落,运动品牌行业正在发生一些变化,Alo Yoga、Vuori等新兴品牌突飞猛进, 跑鞋正在成为 全球增速最快的细分鞋服品类之一,低调老牌选手亚瑟士在疫情后增长迅猛,连运动品牌面向大众的叙事逻辑都正在发生变化……
本期《硅谷101》,主播麻花将对话懒熊体育的内容负责人郑浩榕,探索体育户外运动的业务逻辑与暗流涌动:上一代新星为什么走向低谷,新品牌靠着什么迅猛狂飙,这个品类又会有怎样的成长烦恼。它们的起起落落可能不只是公司本身战略的问题,更关系着人们怎么参与运动、又怎么消费和享受运动。
以下是这次对话内容的精选:
01 lululemon的增长瓶颈:红利见顶,对手紧逼
麻花 :lululem on一季度 的净利润同比下滑2.1%,它们这是2021年以来第一次净利润下滑。同时中国的同店销售额已经从去年同期的增长 26% 降速到7%。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看待lululemon增速见顶的这个问题的呢?
郑浩榕:lululemon作为一个女装起家的品牌,从成立到现在,在25年的时间内卖到了100亿美金。这是非常强的。它在大概十年前开始做男装,而男装做到头也就是25个点左右,之后很难往上爬。鞋类以及其他类目最多到15个点。它是靠运动功能特质做出来这家女装,在这个变化非常快的产业里要做到这个体量是非常难的。
lululemon的波动性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女装的上限比男装要高,而当这个速度跑起来非常快的时候, 带来的问题就是波动非常大。第二个就是人群以及时代的变化。lululemon其实也是踩中时代的红利。之前它们创始人Chip Wilson自己也有讲,他做这个是来源于在97、98年的时候看到了当时的新女性。
基于这个人群观察,他将她们梳理为super girls。而这个人群是在变化的。再者就是时代的变化,我举个关于Alo定位的例子,有评论曾经开玩笑说,Alo定位是lululemonlemon用户的女儿。
麻花:Alo的用户的定位是lululemon核心用户的女儿,年轻一代?
郑浩榕: 对,但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Chip Wilson后来说 super girls的定位差不多是在24-35岁之间。现在正好25年过去了,当时出生的人就长到了这个年纪,但是不一定是super girls的女儿。我认为这个是代际问题,但是super girls这个人群肯定还是存在的。但是你看现在Alo去切割市场的时候讲的概念是It girls(指的是在某个时期特别受关注、被认为有时尚影响力、性感魅力或潮流感的年轻女性)或者白女,又变了一个思潮。而lululemon现在只是在过品类,往一个更传统的大公司去转。
lululemon的问题就是消费者的身份认同是否一直在弱化?曾经的红利是不是在消失?另一个点就是,lululemon在13、14年进军中国的时候恰好赶上经济上行期,当时的女性更可能对品牌产生认同感。现在整个环境变化之后,是否还能有这种认同感?这点是存疑的。如果品牌在出现这种问题后没有对用户定位进行延展,很可能会遇上一些新问题。
麻花:它在北美的增长见顶可能是因为什么?
郑浩榕:刚才我说的两个都有,包括北美消费大环境也在改变。另一个点就是来自对手的冲击,比如Alo和Vuori。
关于这个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从商业竞争角度出发,因为Alo和Vuori这两个品牌在北美的门店都是追着lululemon开的。它们在国外拓展的时候也用的是这个策略,未来在中国会不会也是这样呢?这相当于直接抢夺lululemon的客群,在lululemon完成市场教育后,Alo和Vuori就踩着它的肩膀上去。
这也和我刚刚说的女装有关系,当女性消费者在买了你二十年之后,确实会产生一定疲劳感。所以当类似品牌在周边出现时,会导致一部分客流的丢失。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就是Vuori一开始是以男性的lululemon这个定位起家的,但是它们在2018年推出女装,并且官方是说它们用三年时间将女装比例做到了50%。这说明他的产品很快吸引到了女性用户,并且不用做太多市场教育的工作。
去年外界对Vuori的营收评估大概是在10亿美金,Alo大概是在15亿美金左右。大家以为Alo是爆火的新牌子,但是它其实是在2007年成立,到2020年营收才大概到2亿美金左右。但是用5年时间将主要增长做到了15亿美金,这是非常夸张的。
这两个牌子的营收加起来,假设有一半份额是从lululemon吃掉的,以lululemon现 在100亿美金的收入来说,它们大概可以吃掉15%左右的份额。这可能就是直接对手对lululemon的冲击 。同时北美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垂类品牌竞争是很激烈的。近五年其他垂类品牌的崛起也吃掉了lululemon一定份额。所以说,lululemon的这个问题有它本身的,也有来源于竞争对手的。
麻花 : 明白,所以在 谈到lululemon困境的时候,主要就是几个点。 一个是lululemon本身定位在运动功能女装,而女装本身是一个做到百亿再往上走就比较难的一个品类,可能会增长得很快,但是天花板也就在那。第二个点是你提到了lululemon品牌泛化以及新品牌冲击的问题。
02 运动品牌的周期宿命,难逃的扩张陷阱
麻花 :lululemon现在这个情况让我很容易联想到安德玛。它的创始人以前是打橄榄球的,品牌的拳头产品是速干衣,安德玛创立之后曾经连续很多年每年的营收增速都在20%以上,在美国的市占率还曾经一度超过了阿迪达斯。
但现在去看,它去年卖了52亿美元,营收同比下滑了9%,还亏了2亿美元。股价最高是到过50多美元,现在也就6、7块钱。
我个人会觉得lululemon和安德玛还是有一点相似,因为它们创立的时间都差不多,一个是1996年,一个是1998年。做的都是垂类人群,单一品类起家,而且都一度被认为是要抢阿迪和Nike的饭碗,突然之间都增长不上去了。你觉得这是不是垂类运动品牌想要进一步去寻求增长时很难避免的一个成长烦恼呢?
郑浩榕:它们之间确实有点镜像的情况。安德玛是做上衣起家,偏男性健身,之后切入了橄榄球、篮球、跑步以及女性。lululemon是裤子起家,偏女性瑜伽。它其实也做健身跑步,包括高尔夫,也切入男性领域。但是我如果回头看,我会觉得安德玛在2010年左右是高峰。后面的这十年,我的理解是安德玛太想进步了。安德玛跟lululemon有一个相同问题,就是安德玛的创始人Plank,外界后来对他认知会觉得他在13、14年之后太想快速扩张,想赶紧上规模,赶紧把自己的体量做起来。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正好它作为一个美国公司,切入的那几个板块在北美全部都要跟Nike去正面抗衡。你作为一个新秀去跟一个老大在北美大本营去跟它对抗,我觉得当时是承压很大,明显没法跟Nike真正地去在各方面的投入上去匹配。
安德玛在篮球跟跑步上的产品开头都不错,但是即便现在安德玛的篮球还有库里这张牌,库里也快退役了,而且它也只有库里。安德玛跑步刚起家的时候,其实口碑也都还行,但是就是后劲不足以及女性产品口碑也不好,导致后面整个的定位又越来越模糊。
还有一点就是海外市场也没有去帮它补充一点及时的营收跟利润,导致它很快在15、16 年之后开始进入了恶性循环,为了处理多余的库存就不断打折,进奥莱,最终导致利润下滑又拉低了品牌档次。这也导致它没有余力去吃到运动休闲风和户外的这些红利。它利润都不行了,自己内部的Plank又出了点事,到后来又被SEC(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缩写,译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去查,风波不断。
相比而言,lululemon目前的状况要比它好。第一就是lululemon的男性产品以及在男性之间的口碑是要比安德玛在女性方面做的好的。第二就是海外中国市场整体也还行,能够支撑lululemon有很好的一个增长点。lululemon的管理团队从17、18年之后也相对稳定。我觉得它们处境是相似的, 但是lululemon内部肯定也知道要有前车之鉴,实际上就是看最后怎么在市场上去做真正的突破。
麻花:你有接触过真的能够克制住不去进步的品牌吗?
郑浩榕:我们来看家族企业,可以看New balance和布鲁克斯。布鲁克斯曾经也想过,但是后面也收回来了。现在在北美做得不错,但是后面也慢慢出来了。我不好判断这是不是克制。New balance这个百年品牌一直是以跑步为主,当然近几年也能看到它们在做其他品类,所以不能完全说是克制。
严格来说我觉得很难。因为站在老板的角度,其一是大家都有危机感,有想要往上走的雄心。其二是不进则退,当你想克制自己的时候,市场不允许你这样克制。
麻花:那我们再说两个品牌,绝对不是家族企业,也绝对不克制,就是Nike和阿迪达斯。Nike前两年的业务是很不理想的,但是因为最近换了一个新的CEO,业绩和股价都开始有所好转。阿迪达斯之前也是经历了比较严重的库存危机,但是现在又成功地把自己包装成了运动品牌里面最潮的那一个,为什么阿迪达斯和Nike可以熬过那么多轮的波动周期呢?
郑浩榕:大概在1950年左右,亚瑟士跟阿迪诞生了。阿迪兄弟分家有了彪马,亚瑟士后来就孕育了Nike。等到大概是70到80年代的时候,Nike在北美先后打败了匡威跟阿迪,然后在跑步,篮球市场上慢慢起来,1984年签了乔丹之后,正式进入上升期。那个时候后面第一个出来挑战的是锐步,它是一个通过钉鞋起家的英国牌子。
但很多人不知道锐步是最早的在女性运动这个领域抓住机会的品牌,它是通过女性健美操这个风潮进入美国的。之后它很快就跑去做篮球,也曾一度威胁到了Nike跟阿迪在美国的情况,但是后来的命运就是阿迪就直接把它给收了。阿迪觉得说,反正我收了你,正好可以跟Nike去对抗,没想到最后效果不好。
第二个挑战者就是刚才说的安德玛了,1996年诞生,2010年左右是它的巅峰,就在后面这十年对抗没有跟上,挑战失败。再往后就是lululemon,大家其实很多时候说的是lululemon市值最高的时候比阿迪高,但是你如果只看营收这个大盘子的话,其实这30年来只有Nike跟阿迪能够真正地形成对决。阿迪也是从足球起家的,Nike是跑步起家,它们也是一个单一品类、单一人群起家的,扩品类、扩区域。
麻花:对,但是为什么它们行了呢?
郑浩榕: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说的时代红利,在它们更早之前,体育在全球都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一个点还是体育营销这个事情。在70到80年代整个的电视转播还有媒体环境的变化之下,职业体育的发展把环境重塑了。
其实你说更早诞生的亚瑟士、匡威、锐步、卡帕这些老的牌子,反而出现得太早了,所以它们后面的命运比较颠簸。但是Nike跟阿迪正好抓住了60到80年代这一波的世界潮流。它们抓住了体育资源还有传播资源,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你回到产品上说,它们真的是比其他品牌强很多嘛?我觉得这未必,但是在当年那个时候,它们在体育资源跟传播资源的利用上成功帮它们建立了近半个世纪的领先优势。
这种头部效应就是运动鞋服领域跟别人的很大不同了,一旦站住了这个位置,那就是站住了。当然也有挑战它们的人,但是要不就是自己没有扛住,要不就是被收购了。
所以它们在扩品类、扩区域的过程中,第一就是扩品类。它们产品线和牌多。第二个就是扩区域。Nike和阿迪作为最早吃到亚洲跟中国红利的品牌,每次在北美或者是欧洲遇到收入问题的时候,它们经常会把中国拿来作为一个保持增长的来源。阿迪跟Nike确实是最早进来,而且也在中国市场拿到很好回报的两个品牌。所以我觉得扩品类和周期的时候,为什么它们是吃到一定时代红利的。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阿迪和Nike跟lululemon、安德玛不同的是它的核心在于鞋。所有的分析师去分析Nike跟Adidas的时候,无论他分析是跑步还是篮球,核心都是从鞋分析,鞋的收入通常来说是占大头的。
第二就是说鞋更容易损耗,所以它对所谓的技术的要求更高。鞋这个领域是比较容易建立门槛的,整体的运动鞋服你说它科技含量很高吗?其实并没有。本质上还是一个材料技术的变化。但是在这鞋跟服里头,鞋肯定还是要高于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鞋它是一个支撑性品类,以鞋起家跟以衣服起家的品牌差异到后面会越来越大。这也是安德玛跟lululemon的一个劣势。衣服太容易有潮流跟波动了,鞋虽然也有,但是它会比衣服更有门槛一点。
所以很多时候通过鞋来建立专业性,建立自己的品牌,再辐射到服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打法。阿迪跟Nike就是这么一个路数,所以它现在鞋的比例还是非常大。它们最近十年遇到的问题其实都是在于它们卖货卖到不见棺材不掉泪。阿迪卖boost跟Yeezy卖到疯为止,然后才愿意去认真地去想要怎么处理?Nike 就更不用说、Air Force1、AJ 1跟Dunk非得卖到消费者腻了它们才愿意收手。
但是你回头去看,给它们带来最大收入的是鞋,然后它们遇到的问题是库存太多了,不收手的也是鞋。
所以当投资人去看公司有没有回暖的时候第一反应还是去看Nike有没有出新的鞋子?阿迪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因素是很重要的。阿迪跟Nike也做过收购的事情,但是很难。Nike到现在就只剩一个匡威,阿迪甚至都没有了。阿迪宁愿去做自己的三叶草也不需通过收购这个方式来维护自己。因为每次买回来之后就得卖掉。
但是安踏是追赶者,必须走多品牌这条路去追赶它们。所以安踏跟lululemon、安德玛的方式又不一样。从追赶者的角度来说,相较于lululemon跟安德玛那种想通过衣服起家来追赶的方式,可能安踏的收购方式胜算更高一点。
麻花:现在Nike和阿迪它们鞋这个品类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郑浩榕:我没有具体数据, 但是肯定是超过一半的。
麻花:你刚刚还提到一个点,Nike和阿迪它们产品库里随时都能拿出来一个用,这个有例子可以分享吗?
郑浩榕:我刚才说了三大卖得好,Air Force跟AJ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然后拿在那里可以卖这么多钱。阿迪的三叶草以及后来在卖的这些接班的鞋款,全部都是在60年代左右出现过的鞋。它们可以直接拿五六十年前的鞋来做复古然后又成为一股潮流。
我觉得这个是最典型的,但这个东西要取决于走的是运动生活或运动时尚的路线。需要注意的是,消费者依然要求你在专业运动线上要拿出新的产品跟表现,如果你还是吃老本,那他必须要看到变化。所以这些专业产品线在老的品牌内部反而压力是更大的,因为面临老化的问题,它不像那些复古的。
03 Alo崛起,社媒品牌杀出重围
麻花:现在想讨论一下lululemon的主要新对手Alo和Vuori这两个品牌。先介绍一下,Alo是一个主打美国白女的运动品牌,目前全球130家店,绝大部分都开在美国,而且在离lululemon门店非常近的地方。这个品牌营收已经到十几亿美元了,主打的是好看。
Alo至今没有进入中国的内地市场,并且在网上的评价也两极分化。喜欢的人会说设计得很好,格调非常高,但是不喜欢的人就会质疑面料和裁剪。我想问一下,你觉得Alo会不会是一个更擅长视觉营销而不是功能营销的品牌呢?
郑浩榕:Alo的门店特性还蛮强的,进去能明显感觉到在色彩和款式上和lululemon有很大区别。它和lululemon形成的视觉冲击是很明显的。
它的功能营销我确实想不出什么记得住的点。运动品牌最终无非是要靠独特性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从鞋服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一种快消品。先抛开管理跟运营的因素,我们简单粗暴地理解为运动品牌是一个技术功能性加品牌的合体技术,比如材料设计再加上一个供应链品牌,这里头就是你掌握的体育资源,无论传统的或者是新型的。
另一个就是传播渠道,运动品牌就是体育资源加传播渠道的总和。有时候我们可以把线上线下的销售也视为一个广义的传播渠道。那就是一个品牌在这四个子集上有没有产生新鲜感或独特性?我觉得起码Alo在设计上还有传播渠道上能够给你一些冲击的点。但是这个打法搬到国内就是小红书品牌,起码是用小红书来壮大的一个品牌。因为它是个07年的品牌,但是到20年左右它都还是一个2亿美金体量左右的公司。
麻花:正好2020年的时候TikTok非常火。
郑浩榕:对,它就是TikTok加Instagram。我记得Alo自己的高管就说,我们就是一个社媒品牌,所以它的功能营销我就很少听到,通常会出现在评论区,不会出现在它们主观的传播里头。
麻花:我们再说一下Vuori,它是一个做男性瑜伽产品起家的品牌。门店数量不到100家。软银曾投资过它,在去年底完成了8.25亿美元的融资,现在的估值大概是55亿美元。你觉得Vuori是靠什么另辟蹊径的呢?
郑浩榕:相对Alo来说,我觉得它更稳健一些。成立的年份包括发展轨迹相对更稳健。而且它早期的策略是像lululemon一样,做更多的社群。这种社群也不一定是运动,最重要的是连接感。
同时因为它是个加州的品牌,最早营销的那个短裤是有点沙滩运动属性的,所以它起步的时候是基于运动这个场景来打的。而且它在中国的策略我相对会认可,从进入的时间点、开店的速度以及战略来看,它对自己的定位是有一定的把握。这种克制在现阶段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非得跟Alo比的话,我觉得它比Alo的发展前景更好。
04 昂跑与Hoka两位数增长背后:丑鞋经济与黑科技
麻花:再说一下跑鞋,正好跑鞋这个品类在全球范围内都特别火,特别是昂跑和Hoka这两个品牌,大概每双鞋是千元人民币以上。但是在现在这个大环境里几乎每年都能保持双位数的增长,这个整体增速是非常快的。那到底是跑步的人多了,还是把其他鞋换成跑鞋的人多了?
郑浩榕:我觉得这两点都有,跑步的人更多。基础背景就是老龄化这个全球问题,特别是在发达国家里头。但美国不一样,它永远有新的移民,但是美国的主力消费人群其实也在老龄化。
中国也就不用说了。门槛低以及疫情的影响,导致大家对跑步的需求更高了。第二就是,Nike自己公开承认北美的市场被Hoka跟昂跑拿走了跑鞋的份额。
麻花:昂跑和Hoka这两个品牌为什么能够抢走Nike那么多的份额?它们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郑浩榕 :回到刚才说的新鲜感或独特性的话,起码昂跑跟Hoka在材料跟设计上是给人家一个视觉的冲击。 Hoka的厚底一开始也是被人叫丑鞋,但丑鞋已经太火了,现在被说丑鞋好像是褒义。
麻花 :东西越丑越火。昂跑它有个鞋底有很多小洞,很多人也是觉得丑。
郑浩榕 :对,但是你说其他牌子丑鞋就是风潮吗?所以我觉得视觉上给到的冲击力就是匹配后面的整个体育资源加传播渠道的。就品牌建立来说,因为昂跑跟hoka都是运动员来做,起家也都是通过非常细分的运动。几乎都没有找明星或者是大牌的运动员。
费德勒是属于另外一种性质的代言,而且费德勒的加入也是等到昂跑发展到了一个需要去往更大的圈层的时候。 Hoka更重要的还是抓到了越野跑这个细分的赛道。昂跑的话身份属性建立得更好。
麻花 :昂跑和Hoka的鞋底不仅是视觉冲击力强,还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在里面。比如昂跑的核心专利是cloudtec,Hoka是极厚中底,又被叫做泡沫专鞋,在做专业跑步运动的时候,这两个品牌的核心技术可以提供更好的缓震和回弹,让跑者在长时间的运动中更省力,为足部提供更多保护。
而在日常通勤穿着的时候,这种更好的缓震和回弹也可以提供更多的舒适感,这种舒适感可以好到什么程度呢?在美国,如果你有一些运动损伤,或者膝盖和脚有问题,医生还真有可能会推荐你去穿Hoka。
这种极度舒适的鞋底技术对昂跑和Hoka从垂直领域扩圈到更大范围的普通人群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它们正好是疫情之后的几年发展得特别快,疫情改变了人们非常多的习惯,比如大家会更看重运动带来的健康生活方式。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居家办公后,人们自然而然习惯了穿更舒适的衣服和鞋子工作,再让这些人穿着尖头皮鞋或者高跟鞋回去通勤上班,他们反而不适应了。而且疫情之后,很多中产人群消费更加谨慎了。他们可能会减少大开支,但也不能完全没有东西来作为身份标识。于是他们转向了新一代的跑鞋。你刚刚提到昂跑在建立身份属性这方面做的很好,可以展开讲昂跑到底是建立了什么样的身份属性吗?
郑浩榕 :它一直在强调自己商务场景是可以穿的,但其实这个也建立在价格不能掉下150美金,以及什么人穿。 在疫情后的这两三年里,中国的精英人群其实建立起了我脚上要穿一双昂跑的这种认知。
麻花 :所以Hoka和昂跑还不太一样,Hoka更偏越野跑的一种,昂跑就是更偏向身份上面?
郑浩榕 :起码在中国这个市场来说, 昂跑的身份属性会更强。
麻花 :亚瑟士这两年也翻红了。它是怎么在这种激烈竞争中有一席之地的呢?
郑浩榕 : 2019年对于亚瑟士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它在2019年做了很多变革。最出名的鞋是KAYANO,但是KAYANO的问题是这个最主力的鞋款出现了品牌老化的问题。2019年的时候亚瑟士在跑鞋这个最主要的产品线上推出了新的多条产品线。后面通过了一系列的马拉松赛事,在专业市场做出了很好的名声。
同时,它重新打乱架构做了一个运动风格的部门,像鬼冢虎这种老牌子也开始在那一年全球去做DTC (Direct To Consumer,译为“直营模式”) 。所以它当时在做的东西就是两个,一个是在专业运动上去开启新产品线,告诉用户我有新产品技术了。第二是各种风格的重新组合。其实做的还是那些东西,联名走秀、大牌设计师、网红。跟阿迪在这几年做运动潮流线的时候是没有太大差别的。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吃香了。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亚瑟士有过一段时间的低谷。有段时间没有看到后,大家的新鲜感又回来了。所以亚瑟士这一波,在中国我们这个市场上可能会感知最晚,因为它最早是疫情之后在欧美起来的。
另外一条就是它在运动潮流这块成功了。亚瑟士的二手价格在过去几年都是非常高的。 它是先从欧美跟日 本重新起来,然后再衍生到中国以及东南亚市场,所以中国市场增幅在2023、2024年才慢慢更高起来是因为重新再辐射过来了。它股价从疫情前到现在应该是涨了大概800%。这个牌子的被忽视的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声量并没有那么高,它的势能是在欧美去发酵的。
05 本土品牌的突围之路:乘户外东风,加速破圈之路
麻花 :在这波户外风潮里,闯出了很多中国本土运动品牌,比如说伯希和、凯乐石、还有二普纬度。除了顺应运动户外的大潮,你觉得这些本土的品牌还做对了什么呢?
郑浩榕 : 第一是用好自己的擅长的东西,去强调好功能性跟技术性。中国的供应链跟生产技术可以很好地降低成本。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中国本土牌子有更好的中国版型。现在户外被人诟病的点就是海外品牌版型存在适配的问题。所以你说lululemon做得好的就是有出亚洲版型。所以在版型跟脚型这个领域中国品牌有很多空间。比如说伯希和的抖音太强了。
麻花 :它们在抖音上做得有多好啊?
郑浩榕 :它们的招股书里写2024年抖音的收入是3个亿出头,全年营收是17.66亿。在过去三年大概是不断地接近翻倍的一个过程,它其实很好地卡住了凯乐石价格上调之后让出的这个价格带。
二普纬度在我的认知中一直给我一种设计师品牌的感觉。它还是很强调功能属性的,所以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受众。但是和凯乐石相比,一个新的品牌要马上到这个价位去,难度比较高。
因为凯乐石去做自下而上虽然挨骂,但是大家起码接受了,这也能够支撑起每年的销售额。核心是高举高打之后能够把爆款做出来,它有几款爆款在上面顶着,之后下面的东西即便是价格不高,也起码把品牌顶上去了。
但是品牌顶上去的前提是它做了快20年了,在专业运动领域有积累跟铺垫。所以新品牌一下子上这么高的价格,我觉得在中国这个消费环境下是有一定风险的。
麻花 :我发现一个问题,好像现在进入大众视野的,要么就是像伯希和、凯乐石、二普纬度这样聚焦在户外上面的,要么就是像Maia Active这种女子运动。为什么是这两个品类?
郑浩榕 :其实篮球、足球也有人在做。但是这种最传统的品类,体量做到大概10亿就是一个坎了。后面进一步的管理跟运营难度会加大很多。户外这个风潮确实体量太庞大了,这股风潮是远超于其他垂类的。
高尔夫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所有传统的高尔夫品牌体量都不会太大。网球方面全球最高的网球选手还是阿迪, Nike在签,再往下很多时候卖的还是装备。在鞋服这个角度,没有一个垂类的。
它可以做到一个小而美的生意,但是要做到户外跟女性这个体量跟声量的话是相当难的。其他的品牌想去做网球风跟高尔夫风的东西,其实都很好做。最终还是得回到那个点,比如体育资源和传播渠道的差异化。
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还是没有这些土壤。户外跟女性确实是不一样,女性品类有运动的成分,但到后面还是一个女装穿搭的部分,这个远比任何运动品类都要庞大。但是难题就是再往上做竞争也更为激烈。
疫情之后叠加了户外这个属性,整个社会的风潮就是日常通勤、商务都能穿。冬天这些外套被置换成了户外的品类。这个体量是因为冬天保暖是刚需,所以说冬天的品类会导致这些户外品牌更容易破圈。
麻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本土品牌被视作是某些国外同类品牌的平替。但是现在凯乐石也不是很便宜,这种提价行为是本土品牌在继续发展的路上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吗?是要为了什么而去提价呢?
郑浩榕 :首先敢于提价跟愿意提价的一个原因是用户人群在扩大。更有消费力的那群人愿意来、买得起,整体需求上升带来的这个窗口期是要抓住的。
提价就是一个品牌向上的手段。 如果不提价,只能去提效率。但是在中国这个方式是没有太大空间了。Zara、优衣库,迪卡侬这三家在中国都被卷到不行了,所以中国品牌在这个模式上精进,难度也是比较高的。
提价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工程。迪卡侬也在搞提价,但是为什么提价之后会有遇到一些品牌方面的问题,就是迪卡侬这个体系过于庞大,提价难度太大。
但是对中国品牌来说还有一些空间。更现实的提价是为了利润,品牌要向上,首先要有利润来支持你做更多的事情。
我的现金流不可能全部拿出来花掉。而且只有这些钱花出了效果,提价才有可能真的能帮助你品牌向上。然后凯乐石它是硬顶上去了,第一原因是确实有这个人群愿意来消费。
第二就是说过去20年在这几个专业运动领域的投入是能够讲出一些故事来支撑的。它现在去做运动员国内外的赛事,我觉得是有在花心思的,起码它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一部分的消费者。肯定有人骂它,这是一定的,老的用户抛弃它也是一定的,但是它肯定知道核心任务是在这个窗口期抓住这批认可我的,愿意为我花高消费的客群。
所以我觉得凯乐石是在这个点上想清楚了,所以敢高举高打。当你回头看凯乐石,有时代的成分,也有环境的因素。所以让它有这么好的一个发展的环境。
麻花 :你觉得现在我们本土运动户外领域的创业者,可以怎么样避免尽早地陷入这种成长陷阱里面?
郑浩榕 :我觉得大家都想进入成长陷阱,因为你首先得有增长,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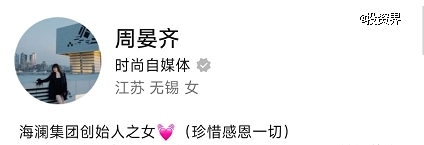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